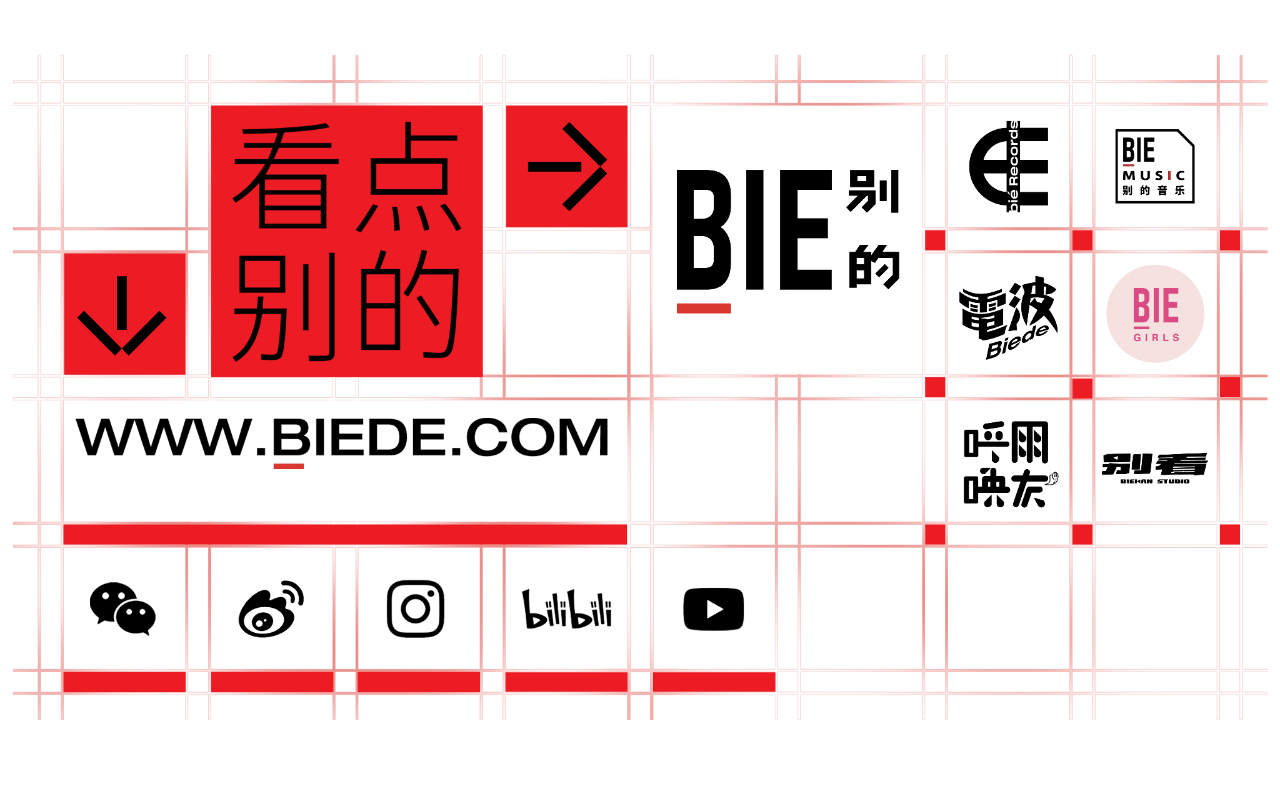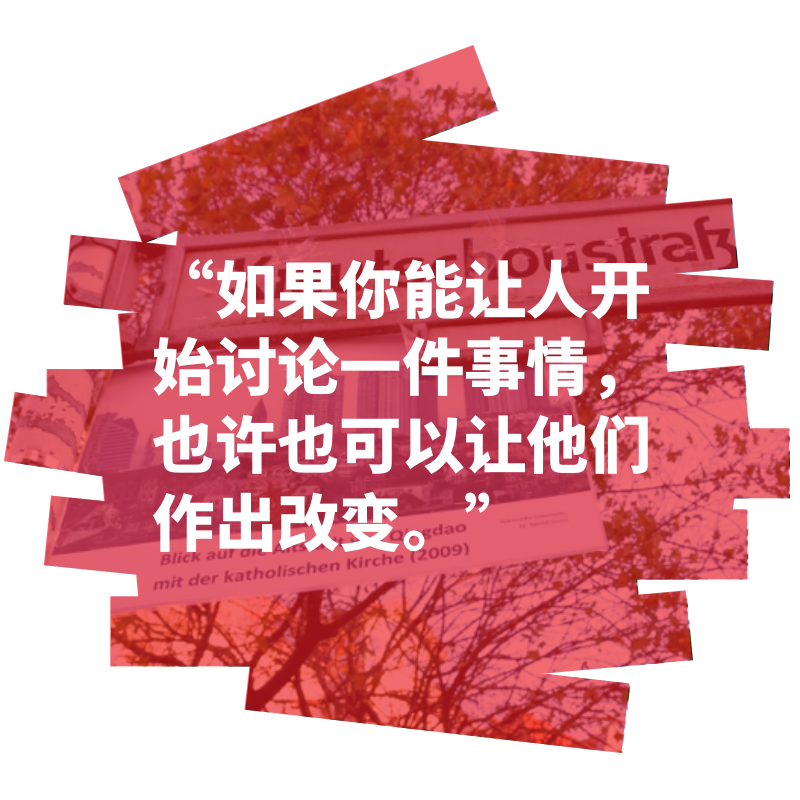



位于柏林 Wedding 区的胶州路。图片来源:明晔

《时局图》


2020 年 6 月,柏林人自发参加 Black Lives Matter 抗议活动。图片来源:明晔


柏林胶州路和萨摩亚路交叉路口。图片来源:明晔


北京花园前的一个导览牌被志愿者们贴上了关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图片来源:明晔

图片来源:明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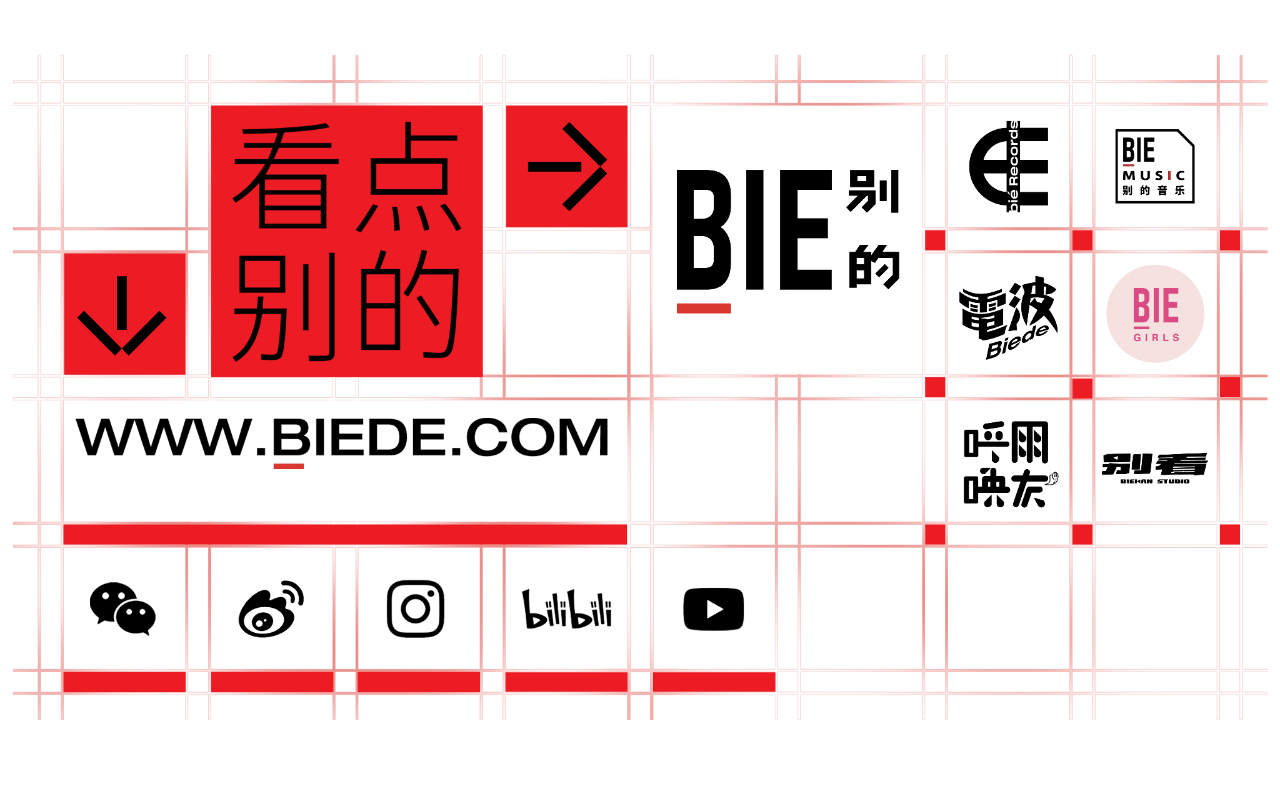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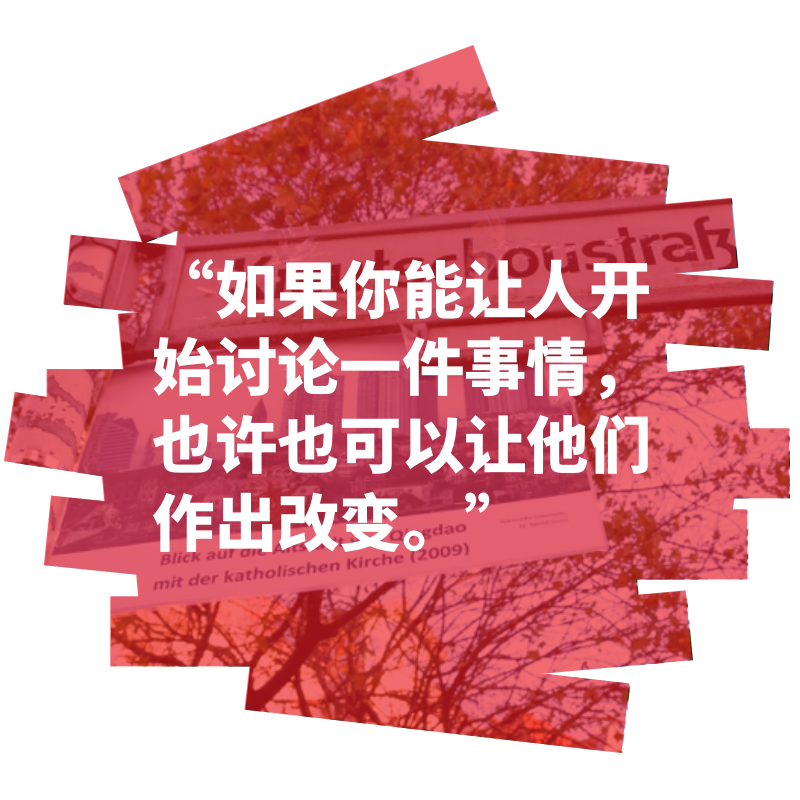



位于柏林 Wedding 区的胶州路。图片来源:明晔

《时局图》


2020 年 6 月,柏林人自发参加 Black Lives Matter 抗议活动。图片来源:明晔


柏林胶州路和萨摩亚路交叉路口。图片来源:明晔


北京花园前的一个导览牌被志愿者们贴上了关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图片来源:明晔

图片来源: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