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艘艘木筏顺流而下,将长江中上游的木材运送到下游城镇。林农、地主、伐木工、船工、牙行、钱庄、榷关,以及商帮与行会,组成了一个跨区域的庞大市场……通过木材的贸易与再生,森林仿佛“流动”起来,满足了整个清代中国的房屋、桥梁、舟车建造等需求。《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一书讲述了这个庞大的市场如何运作,揭示了清代森林可持续发展的奥秘。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讲述了明清两代的皇家木材采办的情况,澎湃新闻经光启书局授权发布。
明代的皇木采办
15世纪初,明代第三位皇帝永乐决定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这给朝廷的木材供应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南京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是自宋代发展起来的木材贸易网络中蓬勃发展的枢纽,而新的都城位于森林砍伐殆尽、远离木材产地的华北平原。在明代的头几十年里,由于战乱危机、人口减少和不利的财政政策等因素叠加,市场和商业普遍衰退,这也限制了国家在市场购买方面的选择。明廷建设新的都城需要大量巨木,这一迫切的需求进一步加剧了皇木采买的困难。宏伟的宫殿和庙宇需要尺寸巨大且质量上乘的木料来建造承重的梁柱。获取巨杉已然困难重重,而明代的皇家美学更将楠木视为皇家建筑的绝佳木材,这种珍贵稀有的树种只有在中国西南一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才能找到。如此巨大的需求给伐木和运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明初,国家通过两种途径获取木材。它最初在榷关向运送商用木材的木筏征收过境实物税。由于明初区域间木材市场的规模有限,这些实物税并没有为国家带来多少木材,更不用说至15世纪晚期,这些实物税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以白银支付的货币税收。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它们无法满足国家对大木的需求。因此,明廷常常不得不采取第二种方法,即直接从偏远的森林(特别是西南诸省)采伐大木。当一个重大的土木建设工程开始时,朝廷会委派专职官员督办招工、山脉勘察、砍伐和运输的整个过程。在15世纪早期,用于修建北京紫禁城的巨木是从四川、湖南和贵州的老林中砍伐下来的。嘉靖(1522—1566)和万历(1573—1620)时期,朝廷在这些省份搜寻大木的活动达到另一个高峰。然而,到了16世纪晚期,由于楠木的供应量大大减少,已不再可能完全用楠木建造大型建筑。楠木仅仅被用于建造最大最显眼的梁柱,而建筑结构的大部分则用杉木建造。在16世纪,明代的经济整体上已经从开国初期的困厄中恢复过来,并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历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商业革命”。这次变革持续到18世纪,虽然有些许中断,但在规模和范围上超过了之前的唐宋转型期的商业发展。生产力的稳定增长和全国性工农业品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区域专业化。国外白银的流入促进了贸易的货币化和扩张。木材的生产、交易和消费都是这一宏观发展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聚落的扩大以及区域生产专业化的加深,木材消费的地方性减弱,变得更为依赖跨区域贸易。到15世纪晚期,跨区域的木材市场已经开始恢复到宋代的水平,将江南的消费中心与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的森林连接起来,木材生产也成为专业化的地方产业。宋代出现的商业造林扩展到更多的地方。专业的林场致力于栽培树木,将砍伐的木材供应远方的消费者。虽然常规林场足以提供普通尺寸的木材,但大木潜在的高利润吸引了商业资本将木材贸易网络扩展到更偏远的原始森林。西南山区在明初是官员探寻皇木之所,而到了16世纪,投机的木商们也常常接踵而至。
活跃而广阔的木材市场为朝廷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不必直接参与伐木的过程。在16世纪,朝廷越来越倾向与木商签订木材采购合同,后者收取官府的资金,并按照要求交付特定数量和品种的木材。到明末,国家通过这些商业代理人在市场上购得大部分的杉木。国家转向市场采购和木材贸易的扩大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只有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国家才能开始倚重商人,但一旦确立了代理机制,国家的订单和资金会进一步推动商业资本向西南的扩张。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成熟,其稳定的木材供应足以满足国家的大部分需求,国家也就不必直接管理森林或监督伐木过程。这些趋势一直延续到清代,那时国家从市场购买木材的方式已衍化为一种常规制度。
帝国扩张与边疆的木材贸易
西南边疆被纳入跨区域的木材贸易体系,这不仅是经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也是明代国家扩张这一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起初,西南边地在蒙古人入侵南宋的军事行动中沦陷,之后历朝历代逐步将其置于更严格的行政和军事控制之下。明清统一西南地区的行动源自多个动机,包括抵御蒙古和西藏的威胁、获取矿产战略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通过汉人的迁居来缓解人口压力。这片广阔的区域——包括后来变成行省的贵州、云南、四川的山脉,以及广西和湖南的西部——并非杳无人烟,而是千年来不同民族的定居之所。虽然官方史书呈现的是民族同化的宏大叙事,但历史学家业已揭示出,帝制晚期的国家集权统治的努力不断受到当地群体和环境能动性的抵制、调和与制约。明代遵循先制,在西南通过土司制度承认当地世袭土著首领的统治,从而实现名义上国家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明代和清初,国家采取各种军事和政治策略来处理地方起事、分化大土司的势力以及限制他们的自治权。明代还在西南地区推行卫所制和军屯制,鼓励汉人从中原向西南迁居。这些措施在18世纪初达到顶峰,清代的雍正帝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一运动曾在明代和其父康熙统治时期以有限的形式开展,此举旨在废除土司,改由国家任命的流官直接进行行政管理。然而,雍正帝雄心勃勃的举措却引发了苗民的起义,清廷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将其镇压。与这场镇压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明清朝廷在西南开展的其他大规模军事行动都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情报收集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当初为了便于国家的军事行动而建设、整修、疏浚的道路和河流,后来成为便于平民和商品流动的必要条件。有关当地环境、交通线和民族志的志书,无论是官方编纂的还是民间商业性出版的,都为前往西南的旅行者提供了指引。随着国家的军事介入、行政改革以及断断续续的移民计划的开展,西南边疆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环境变化。
汉人木商前往西南日益便利,与此相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当地局势更好的了解,以及他们更熟悉的行政架构的建立,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国家扩张的副产品。位于贵州东南和湖南西部的沅江流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山区森林密布,苗民世代居住于此。18世纪,在雍正皇帝军事镇压了苗民起义之后,沅江流域开始为国家和民间提供大量的木材。朝廷在刚刚平定的“苗疆”上建立州县制度,引入了汉人商贾所深谙的行政原则以及儒家士大夫的权威。汉商们知道如何与士大夫打交道,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能得偿所愿。
在18世纪30年代平定苗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动员当地劳工疏浚沅江上游的河道是该地木业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疏浚工程本是为了促进军队调配和物资运输,但也为沅江河谷的森林资源开辟了进入长江水系流域的运输路线。自此之后,沅江地区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苗木”或“西湖木”,在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和清廷的皇木采办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清代的贡木制度
随着康熙最终平定了华南和西南的三藩之乱(1673—1681),清廷终于有了获取南方森林资源的可靠渠道和财政手段,可以借此来重建毁于1679年地震的紫禁城太和殿。虽然原定的重建计划是使用数千根楠木,但被派往四川勘察森林的官员们报告说,山中几乎已无便于开采的现产大楠木,而从深山中运输木材又异常困难。1686年,康熙决定放弃前朝那般对楠木的迷恋,转而以松木和杉木替代。事实上,早在16世纪,随着楠木的日益稀缺,杉木就经常作为楠木的替代品被用在明代皇家建筑中。这一发生在康熙统治初年的事件,标志着官方直接督办南方皇木的勘测、采伐和运输活动的结束。此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省以市场采购杉木为基础的常态化贡木制度提供了皇木的主要来源。作为对这一制度的补充,朝廷偶尔会委派官员到四川和贵州的深山中搜采大楠木,但其规模要比明代的楠木采办小得多,这些楠木只是用作建造宏伟宫殿中少数巨大的建筑构件。清代沿袭了在明末已现端倪的趋势,在皇木采办中更果断地选用新的树种和新的采办方式:杉木被选中了,这是比楠木更常见且更容易再生的树种,朝廷可以直接从市场上购买而不必进山砍伐。
清代通行的贡木制度在官方文献中被称作“额木”“年例木植”或“钦工例木”。民间俗称“皇木”。这一制度由工部负责,自1687年遂成定制,一直延续到1911年清覆灭。到1687年,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四省都确定了每年办解木植的数额、木材规格和官方定价。各省岁解的数额到清末一直保持不变(除了江苏的办解数额在1698年有小幅增加)。四省的督抚分别委任一名负责木材进贡的专员,通常是州县一级的官员,后者以指定的官方定价购进木材,并将之运送到北京附近通州的皇木厂。
杉木是贡木制度唯一需要的树种。朝廷每年总共接收7400根标准规格的例木、1200根大尺寸例木。根据原木的长度和圆围,例木被分为四类。根据杉木的年际径向生长规律,拟合每类例木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估算出杉木大致的树龄。然而,对杉木年际生长规律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树龄几十年以上的研究更少。本书使用了2012年一项研究中的树龄—直径模型。在该研究的杉木样本中,树龄最大的在80年左右,周长约80厘米(2.34尺,即树木胸径 0.75尺)。按照清廷的例木规格,它优于第三类但又不及第二类,第二类至少要有百年树龄。
第一类例木是“桅木”,指从上到下均匀粗壮的长木,通常取自已经生长数百年的木植。虽然偶尔会被官办造船厂用作桅杆,但大多数桅木都被用作皇家宫殿、庙宇和陵寝中最大的厅堂的承重柱。第二类例木是“杉木”,是取自百年到两百年树木的长木。它们一般被用作皇家和官府建筑的柱子和横梁,有时被切割成木板用于造船。这两种顶级木材在木材市场上是稀罕物,市场上的木材大多树龄在几十年,它们是商业化的林场种植出的木材。最次的两类例木是“架木”和“桐皮槁”,通常是树龄在20年到40年左右的树木,在木材市场很容易获得。“架木”得名源自它们被用来搭建仪式或科举所需的临时架子。它们在使用后通常会被回收到皇家木厂。细长的杉木通常被称作“杉槁”,“桐皮槁”是杉槁中的优质品种,色泽偏红,有着与中国梧桐相似的树皮,通常被锯开,用于制作家具或器具。
不过,以上所述的这些原木的用途仅限于皇家和官府,并不能代表平民如何使用它们。在民间的木材市场,“桅木”和“杉木”绝对是奢侈品。最常见的交易木材的圆围在1尺到2尺之间(胸径0.3尺至0.7尺),为御用例木规格的四类之下到三类之上不等。在普通的民用建筑中,“架木”甚至“桐皮槁”都可以用作房屋的承重结构。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之间,圆围2尺至3尺(胸径0.6尺至1.0尺)的长木适用于民间造船,后来在20世纪早期,它们被用于制造电线杆和路灯柱子。
理论上,清廷应该根据各省地方物产的情况来分配进贡任务。朝廷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享有一个跨越多个生态区和具有多元地方性的帝国所带来的财富。以贡木为例,对湖南和江西这两个最大的木材出口省份的办解数额就可以这样理解。然而,浙江和江苏之所以被列为办解省份,并非因为它们靠近木材产地,更多是因为两省拥有丰富的财政资源且管理着最主要的木材市场。浙江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贡木体系,是因为杭州在明代就是大运河沿岸的重要木材市场。但很明显,浙江能够采办的木材仅限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所种植的中等大小的木材。其他三个省份需要办解“桅木”和“杉木”,而浙江从一开始就不必供输这些大木。
普通品种的“架木”和“杉槁”是四个省直接从其辖下的木材市场采购的,通常由牙行承办。浙江依托杭州的木材市场,而江苏则倚靠南京,后者是长江下游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湖南和江西都有丰富的木材资源,所以为了降低成本,交易都在采伐地附近完成。在江西,采买例木的任务落在赣州知府身上。赣州府位于江西南部的山区,其木材沿着赣江北上进入长江。在湖南,来自湖南西南部和贵州东南部的木材沿沅江运输,并在常德府汇合,然后进入洞庭湖。清代的常德木材贸易繁荣,从18世纪后期开始,湖南例木的采购主要由常德府佐(同知或通判)负责。
虽然较次等的两类木材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些民间市场获得,但奉命办解“桅木”和“杉木”的三省必须花更大功夫来满足每年额定的要求。湘黔边地平息苗民起义的十年后,即1746年,湖南办解皇木的官员开始从苗疆采办所需大木,这很快成为惯例。湖南巡抚杨锡绂(1700—1768)于1747年解释道:
缘桅杉二木近地难觅,须向辰州府以上沅州、靖州及黔省苗民境内采取;架槁二木则需在常德聚木之处购办,而扎牌架运经历江湖黄运各河,又须备木帮护,以免沿途磕触伤损。
江西和江苏面临的困难比湖南更多。最迟到18世纪20年代,工部开始抱怨江西和江苏所供原木的数量不足且质量低劣。质量上的缺陷有时会用货币折算,负责办解皇木的官员要自掏腰包来赔偿。例如,在1724年江西交付的1400根架木中,质量残次的有170根,负责官员按官价的三分之一交纳了罚金(每根0.067两,共11.4两)。对于大木,数量不足和质量残次无法用财政付款来抵偿,而是必须在未来补齐缺额。每年交付的原木的数量首先根据长度、厚度或纹理上的任何缺陷来折算,由此在账簿上记录下的“完额”数通常带有小数点。然后将这个数值与该省应解额度相比较,如有欠缴则需要在未来补齐。1741年,在当年额解之外,江西还一并交付了先前在1735年、1738年和1739年欠缴的木料,其中桅木14.56根、杉木206.42根。
将原木数量按其质量进行折算的做法促使江苏和江西交付更多数量的小尺寸原木,虽然品等不足,但折量后仍能满足额解要求。例如,江苏在1754年交付的20根桅木都不达标准,但是,这个不达标的问题在补交了10根同样的桅木之后就迎刃而解了。工部对这种越发普遍的做法不免感到担忧。在1765年的一份奏疏中,工部侍郎抱怨道,虽然允许“折算添补”,但日益依赖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御用的大木严重短缺。为此,谕旨颁布了一条新规,要求桅木必须符合标准,“折算添补”的做法只适用于少量原木。朝廷虽然强化了桅木的标准,但考虑到各省面临的困难,对其他等级木材的要求则有所放宽。其余三等例木的解额中,每等又分为三类,第一类遵循与原始规格相同的标准,而第二和第三类的解额标准则略有降低。
江西、江苏两省为应对办解大木的挑战,越来越频繁地依赖木商采买代办。来自江西、江苏的商人代办,同湖南办解皇木的官员一样,经常出入湘黔交界的苗疆。来自湖南、江西、江苏的代办进入苗寨,仍是在当地现有的市场上采买。与明代和清初的做法不同,他们没有直接组织人力深入山林,从采伐、运输干起。1777年至1781年,时任长沙通判的英安被委派负责采购和运输湖南的皇木。他在手稿《采运皇木案牍》中记录了两次采办例木期间的活动和通信,这篇文献详细地描述了湖南皇木采运的做法。在对比了从市场采买大木与直接从林中采伐之后,英安评论道:“惟有桅木最所难得,价亦无定,有十两以上的,有廿两及三五十余两的,总只要有买。去坎青山,盘费浩大,多有坎青山,算来不如买平水的。”这种完全依靠市场的做法仰赖于木材贸易的日益商业化,即便在这些偏远地区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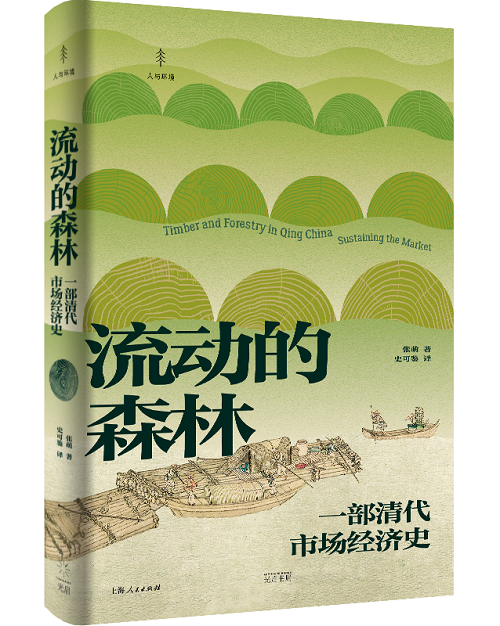
《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张萌著,史可鉴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