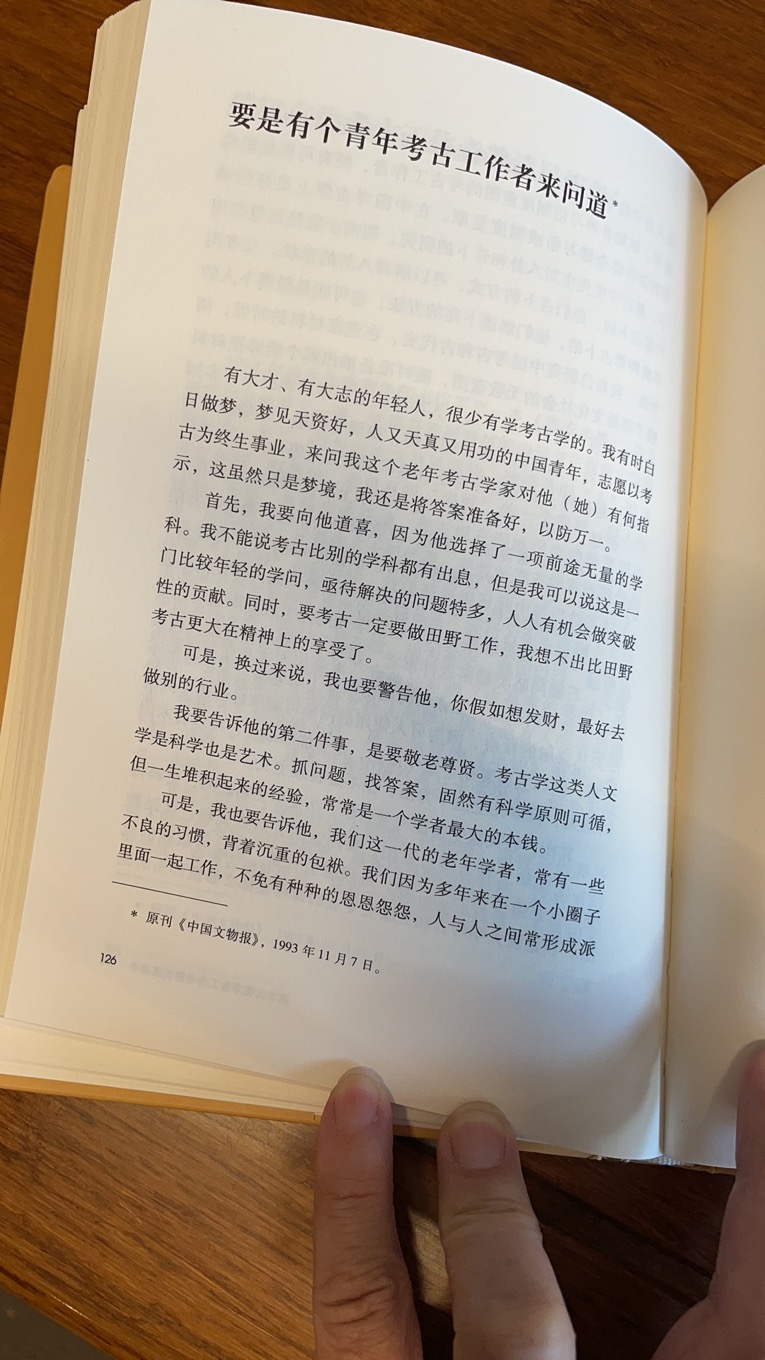三星堆遗址三号坑近似长方形,长约5.5米,宽约2.5米。距今已3000多年。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31岁。
3月16日,当整个坑揭开遮蔽第一次展露全貌,当密密麻麻的文物呈现眼前,他的内心只有震撼。“说不出是为何而震撼,但如果你在这里,你也会与我相同感受。”他说。
徐斐宏博士正在坑内工作。
连日来,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再惊天下”, 上海大学不仅参与发掘工作,也积极承担相关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任务。徐斐宏和他的伙伴们便在其中。
曾有人问他,这算不算最高级别的“挖土”?他并不接这茬,客观回答:“算最细致的吧”。
坑内所有挖出来的土,理论上可以拼回原状
“理论上说,三号坑里所有挖出来的土,我们都可以按原样拼回去,”徐斐宏说。
事情要从1986年说起。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曾在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成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勘探与试掘,又发现了6座祭祀坑。2020年9月起,四川考古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开启了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徐斐宏博士(右四)带领的三号坑发掘团队合影留念。
作为有着丰富田野发掘经验的年轻人,徐斐宏和其他六位发掘人员、两位测绘人员,以及两位文物保护人员开始了“八小时工作制”,发掘、取样、文物保护无缝进行。
8:00到12:00,14:00到18:00,是坑内工作时间,半个月有一天休息。每天上午入坑前,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穿衣服,不仅换上全套防护服,还要戴上口罩、头罩、鞋套。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避免自己的人体组织,落入坑内,造成样品的“污染”。
全副武装的发掘人员,不仅要“挖土”,还要做好发掘记录和汇总。
刚开始挖掘,接触的是填土层,这时候跟当地工人一起发掘,这种算是“粗活”,可也有讲究。在这一阶段,所有挖出的土,按照位置归入网格,每格长60、宽60厘米,所有的填土都会被搜集入库,留待后续整理、研究。
“一般考古发掘不会把填土层全部打包,最多过筛一遍,但是这里的考古意义太重要了,我们不想放过任何信息。”徐斐宏说。
这个填土层,挖到哪里为止,发掘队员心里有数。之前,在三号坑西北角经过试掘,在1.2米深处挖出了铜器,由此判断,坑内其他位置器物层也在这个深度。因此,当填土发掘到1米左右深度,接近器物层后,考古工作便变得愈发细致,多数工作都改由考古队员自己完成。
三道防护,给象牙争取时间
据了解,在三星堆遗址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三号坑内发掘出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个祭祀坑。
三号坑全景。
那么多象牙,如何转移?当被问及此,徐斐宏首先纠正了一个专业术语,应该说是“提取”,而非“转移”。文物发掘出来了,提取和保护,同样是一门大学问。这些埋藏在地下上千年的象牙,含有不少水分,一旦暴露于空气中,若失水过快,象牙的质地就会发生变化。
怎么办呢?站在挖掘的角度,徐斐宏说,目前的技术手段,能做到的有三条。首先,这次发掘配备专用工作舱,简而言之就是坑上造了个高科技玻璃小房子,能控制温度和湿度,为文物的保护提供可控的环境。
其次,在象牙上面先覆盖一层保鲜膜,再覆盖湿的毛巾或湿的无纺布,再往上覆盖一层塑料布,三床被子创造一个湿润小环境。
最后,是人力方面,则是提高工作效率。“这个提高工作效率,并不是加快速度,”他说,再急也要保证耐心细致流程规范,发掘队通过每天加班1-2小时,延长工作时间,尽可能多工作面开展工作,来为象牙争取时间。
在整个挖掘过程中,发现“铜人顶尊”的过程,让徐斐宏印象深刻。
“那是在三号坑最南边发掘出的一件非常罕见的器型。”他说,“当时,这件铜器最早露出土面的是尊的口部,而这个青铜尊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肩部有龙形的装饰,底部圈足下有一块铜板,这已经很特别了,更奇怪的是,再往下挖,这块铜板不是平的,下方收拢的趋势,下面一定还有东西!顺着这个走向,我们从侧面继续清土,发现平板连着的人的耳朵,它与之前发现的铜手十有八九同属一件铜人,进一步发掘果然证实了这个判断。这个发现,是不断刷新认知的过程”,听着徐斐宏娓娓道来,仿佛身临其境。
现场考古,太胖不行?
现场挖掘,动脑筋比体力更重要。例如,在填土层,以小网格方式交错发掘;接近器物和填土层,则改为将坑分成六个大区域,按大网格作业,这样有利于整体把握器物位置关系;到了器物露出后,需要随机应变,合理规划工作路径……一句话,发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策略。这其中的进退分寸,凭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累积。
有人问过徐斐宏,现场考古发掘,是不是太胖不行?因为器物填土层层累积,万一站在下有器物的土层上作业,人太重了一脚踩坏了可咋整?“这是个好问题,”徐斐宏笑着回答,一般是没有体重要求的。换句话说,胖一点也可以的。这个顾虑有道理,但是知道了下面两点,就不会太担心了。
首先,三号坑的土层都是很致密的黏土,踩在上面不容易对遗物造成破坏。同时,现在技术保障更加到位了,三号坑所在的工作舱里安装了工作平台,到了填土发掘的收尾阶段,工作人员不用下脚,而是趴在悬空于坑上方的工作平台上,双手伸出作业,最大限度保护文物完好,不留隐患。“当然这么干比较消耗体力,一般一两个小时就要轮班的。”
现场,工作人员趴在发掘平台上工作。
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博士,先后参加过陕西岐山县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等遗址的发掘,见闻不少,却依然为三星堆考古的科技配置动容。在他看来,联合发掘的指导理念“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贯穿于全过程,考古发掘、科技检测、文物保护,跨越空间配置协调最佳资源。
举例来说,发掘提取的样品,会视情况判定,是直接交付现场的移动检测实验室,还是当地或省外具有权威资质的研究机构。有时候,相同样本甚至会一式多份,分别交给两到三家检测机构,对照分析。最短时间内返回的结果,对现场进一步发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技考古,测测土壤“咸不咸”
当徐斐宏“挖土”时,距离三星堆2000公里之外的上海,有人同步为“土”奔忙。
宝山区南陈路上,上海大学东区十号楼三楼实验室,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马啸教授,正指导学生一起对送来的样本精心分析。
遗物成分分析、植硅体鉴定、微生物监测……他和他的同事们,同样为参与到三星堆的科技考古中而激动。
2000公里外的上海,马啸教授正在分析检测相关样本。
“最基本的,我们会检测送来的土壤的含盐量……”马啸介绍。含盐量?难道考古还要管土壤咸不咸?“此盐非彼盐,”他赶紧解释,与食盐不同,这里的盐,是一个化学概念,主要指硫酸钠、氯化钠、硝酸钠等。对土壤中含盐量的检测,目的在于对文物存储的环境进行判别,对文物现场保护、清理与后期保护等方案提供依据与科学支撑。如果土壤中盐类含量过高,很可能导致盐渗入文物本体中随着水分在内移动,如果遇到环境温度和湿度显著变化,一旦结晶,就可能对文物内部结构的孔隙造成压力,其破坏性就在于此。
除此以外,对一些骨角类文物的显微观察,对判定其性质,以及是否经历过加工、焚烧等也十分重要。而他的同事,对灰烬样本中植硅体的检测分析,可以推测当时的祭祀行为可能焚烧了哪种植物。如此多学科、多单位的参与,不仅是文物发掘保护的过程,也是不同思想视角碰撞的过程。如今,马啸脑子里已经有了好几个研究新方向。
元宵之夜的“连山回锅肉”
“作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前沿阵地,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有很高的科技含金量,各类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手段被第一时间应用于现场,”上海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徐坚教授说,大学能参与其中,对探索新方法、学科建设有很大推进。
他还记得,去年秋天启动的项目,过年暂停,上海大学这支队伍,年初五就直奔三星堆,成为最早到岗的省外队伍。“大家都充满热情,”他说,正月十五,整队人依然工作,下班了一起去吃当地特有的“连山回锅肉”作为元宵聚餐,那滋味至今都觉得特别美。
今年,上海大学新增考古学本科专业,预计从2021年秋季开始招生。他期待着,更多新力量加入这份事业。
采访的最后,请徐坚教授为考古学打个广告,他不假思索,说起业内前辈张光直28年前的一篇文章《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那里面有两句话:
徐坚教授翻到他最先想到的那一页。
“首先,我要向他道喜,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前途无量的学科。我不能说考古比别的学科都有出息,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多,人人有机会做突破性的贡献。”
“念考古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就成了,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 ”
原文地址:点击此处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