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似乎始终是一座充满立体感和阶层差异感的城市。
2014年,青年作家郝景芳的中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横空出世,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阶层壁垒森严的未来都市生活图景。未来的北京被分为三个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相互隔离的不同空间。在小说中,北京的第一空间居住着500万人口的精英统治者,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则是分别拥有2500万人口的中产白领与5000万人口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三个空间平行却不交织,它们分属于48小时中的不同时间段。每到时间“转换”时,前一个空间的居民需要躺到床上接受催眠,此时属于前一个空间的建筑设施将会折叠起来,而下一个空间的建筑则随即展开。
这种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时空立体感,在科幻小说写作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灵感与构思的现实生活来源却更加引人省思。毋庸置疑,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汇聚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与文化精英。国家机关、大型企业、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三甲医院的密集分布,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大量人才的云集,无一不宣示着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精英定位与资源优势。然而,也恰恰是在这样一座资源高度密集且立体的城市,还有许多被称为弱势或边缘群体的人群存在,他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住所与繁华的商圈、气派的政企总部或高档的公寓住宅仅仅一街之隔,却有如“折叠”在“第三空间”,一般鲜少能够被社会媒体关注到。在不少城市管理者眼中,他们至多是需要被进一步“安置”、“疏解”,乃至“腾退”的对象,并不具有深入了解的必要。
英国文化人类学者艾华(Harriet Evans)的新著《底层北京:首都中心的边缘生活故事》(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为我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类很少受到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人群——生活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地区老旧胡同和大杂院里的居民的故事。他们不少是祖辈即居住在此的“老北京”,但也有许多从各地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这些大栅栏居民,往往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在高度拥挤且生活设施简陋的房屋内,还面临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或“文物腾退”所带来的迁居他处的生存压力。作为一个英国的人类学者,艾华在2007-2014年曾多次在大栅栏社区进行深度田野调查。她为何会对大栅栏居民的生活感兴趣?她的这本新书,又为我们理解身处北京城市中心社区的底层人群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处境提供了哪些新的创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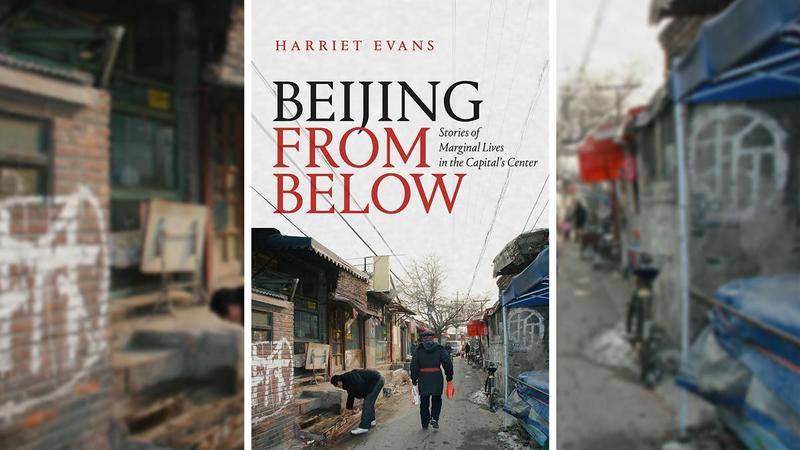
叙事:“庶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在《底层北京:首都中心的边缘生活故事》中,艾华将自己对大栅栏居民的人类学研究定义了三个关键词:记忆、庶民/底层(subaltern)与历史。由于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深入具体社区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察,因此如何处理与定位基于田野访谈所获得的大量口述材料,对呈现本书的预期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作者而言,记忆并非是单纯用来讲述有关过去的“真相”的。在她看来,“记忆的转移与遮挡,实际上揭示了一种为了把握当下意义而对过去进行的一种持续而有选择的再加工”(页4)。这种对记忆颇具解构意味的解读,实际上体现出作者在处理与大栅栏居民访谈和观察所得的材料时的一种理念,即不同人群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个人历史的记忆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同样的事件在不同个体的回忆中,在同一个体的不同时段的回忆中,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个体记忆的选择性与暂时性提示我们,历史,尤其是基于不同个体对“过去”的差异化认知的口述历史,同样存在着巨大的主观差异性。换言之,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理解的“历史”。
那么,普通人或底层民众有自己的“历史”吗?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有着经典的表述,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然而,当我们翻开种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书籍时却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帝王将相和领袖精英的故事。即使在那个异常重视农民运动与农民战争的年代,天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叙述也总是被农民领袖洪秀全和几位“天王”的事迹所充斥;当我们走进定陵地宫参观其巧夺天工的建筑设计时,尽管随处可见告示牌上类似“体现了伟大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的字样,但无论是导游还是一般游客,显然都更津津乐道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之类的宫廷轶事。所谓的历史主体和历史创造者,往往只存在于诸如“人民”、“群众”等抽象的集合性名词之中,看不到形形色色的具体的“人”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的。
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实际上揭示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难题:如何发掘底层民众的历史?我们怎样才能够倾听到他们的声音?对此,庶民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的代表性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早有更著名的经典发问:“庶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Rosalind C. Morris eds.,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nd Ide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21-78.)

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从传统史料的记载中,找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议“新史学”时便早已指出,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只是一部帝王“政治教科书”,读史之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他大力倡导书写全体国民的历史。可是,当我们真正把目光转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时,才发现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是相当稀少和零散的。对此,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史家,常有“文献不足征”的慨叹。当然,一些历史学者已经在积极尝试利用非传统的新材料进行小人物和普通人的研究。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利用大量“个人档案”,出色地揭示了共和国时期若干位有种种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小人物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杨奎松:《“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她的微观史名作《梦醒子》中,利用山西底层士人刘大鹏所著的《退想斋日记》,完整勾勒出刘大鹏与晚清民国半个世纪的动荡相始终中的一生(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笛的《袍哥》则另辟蹊径,在一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1940年代川西平原上的一个袍哥家庭进行了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考察(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这些历史学的微观研究,毫无疑问增进了我们对普通民众的具象化认识,但它们也存在着对文献材料绝对依赖的局限。换言之,这些研究所采用的视角,是高度依赖特定史料的种类与其丰富程度的。当然,如果在材料上无法取得突破,那么视角与方法的转换就显得尤为重要。艾华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直言自己除历史学的档案文本分析与口述历史方法外,更主要的是采用了人类学的民族志式田野调查(ethnographical fieldwork)。为了更好地理解几位大栅栏居民的生活,艾华选择“深入群众”,不但经常拜访受访者的家庭,与他们建立联系,甚至深度参与到一些受访者的家庭事务之中,并成为了大栅栏社区微观生活的一部分,尽管这种“参与”往往并非出于作者的本意,且程度时有变化。由此,作者既是口述史家(oral historian)又是人类学者(anthropologist)的双重方法取径,构成了她在观察大栅栏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时所具有的独特的互补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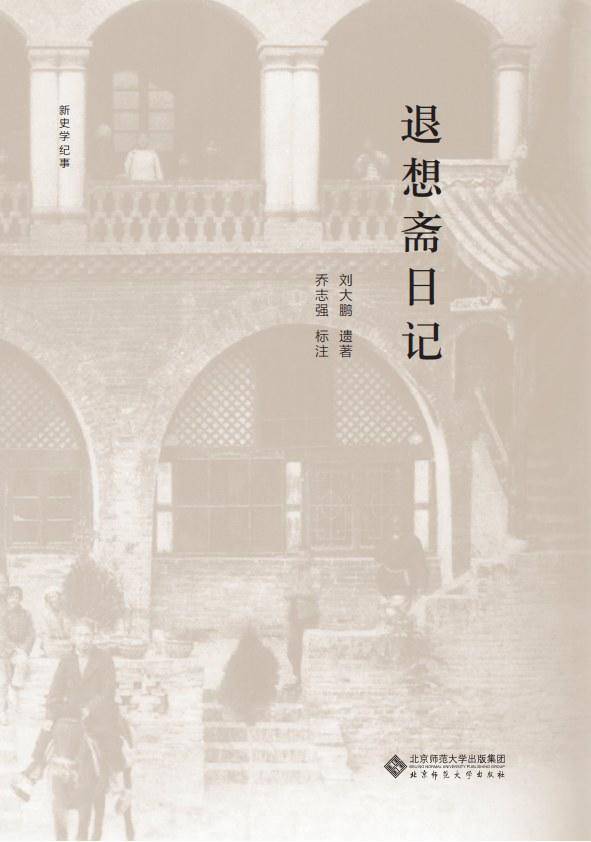
除了学科方法层面的视角界定,艾华对她所使用的“庶民”或“底层”这一概念本身,也有着不同于庶民研究学派的定位。大体而言,庶民研究学派同样强调对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但他们更着重于分析底层群体如何记忆与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认知,尤其是在印度殖民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占据历史叙述主体地位的特定语境下。正如另一位庶民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古哈(Ranajit Guha)所指出的,尽管统治精英主导了主流的历史叙述与多数人的历史认知,但只要研究者注意将被掩盖的底层“失语者”与宏大叙事相剥离,我们仍然有机会发现那些属于底层群体的“历史的微声”(Ranajit, Guha, “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 in Shahid Amin and Dipesh Chakrabarty eds., Subaltern Studies, IX: 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2.)。
与斯皮瓦克不同的是,艾华开门见山地指出,她并不想纠缠于历史学者关注的是否能获取以及如何获取底层声音的问题。在她看来,底层的历史从来都存在于既有的历史叙述之中,只不过其往往被历史书写的霸权者压制在历史叙述的最深处,没有机会浮现到表面。显然,作者对“庶民”的解读更具有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文化霸权理论取径的意味。艾华“更愿意将底层性(subalternity)视为一个可被辨别的轨迹,这一轨迹既在主流系统内,但又抵制其全部的占用”(页6)。换言之,本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挖掘潜藏在主流历史叙述之下,而非横亘在主流之外的底层历史记忆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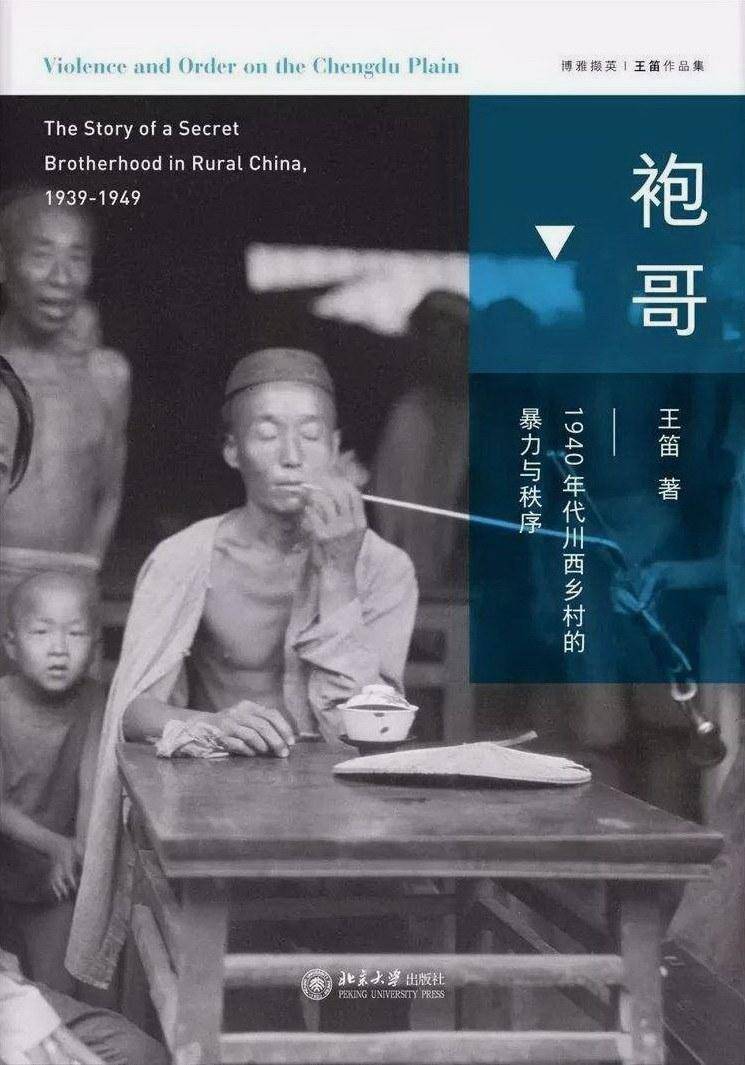
记忆:个体化的历史叙述
作为艾华书中六位主人公之一,第一位登场的高老太太(Old Mrs. Gao),主要是作为个体化历史的讲述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在她的个人历史叙述中,她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遭遇概括为“命不好”:高老太太生于1920年,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孩儿,她还有一个大哥与三个姐姐,但在北京做基层警察的父亲早早离世,没有一技之长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只能艰难度日。还是小孩子的高老太太,很早就学会在地上捡别人不要的煤核来补贴家用。5岁那年,她被母亲送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无所不干。然而10岁那年,经过多次逃跑与送回的拉扯,她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不能再将她送走,于是留她在身边,帮她一起给另一户人家做佣人以谋生。13岁时,她开始自己到铺子里打工;两年后,她的母亲尝试为她找人家结婚,但男方出不起彩礼。
终于,在1937年,17岁的高老太太走入婚姻,正式搬进大栅栏附近的高家。然而,生活的贫困并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善。婆婆无休止地要求她长时间劳动,每天却只能吃到两顿窝头加小碗米饭。在结婚的头两年里,高老太太生下两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她现在有三个子女,两个女生分别生于1942年、1949年,最小的儿子生于1960年,这一年她已40岁,但她跟作者讲:“你得有孩子,不是吗?没孩子怎么过呢?”(页48)
连年的军阀混战与日军侵华,对北京城的底层生活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高老太太在她与作者的谈话中,总能回忆起从死人尸体上捡衣服的“生存策略”。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她才有机会成为一家小制衣厂的临时工,做了几年拆装棉服的工作。尽管收入仍然不多,但总算是稳定,因此每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是面露喜色。1956年,以合作化为目标的三大改造完成,高老太太的丈夫成为“入组了”的集体化菜场的员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对高老太太而言印象深刻,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养活家人。有时,她只能打发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在晚上偷偷去郊区挖野菜回来。到1960年代,高老太太加入了“五七连”,一个为“家庭妇女”提供临时工作的社区组织。她有时糊火柴盒,有时负责折叠印刷厂的书籍纸张,每折100页可以挣2分钱。没有一技之长,无法进入正式的单位或工厂,也就意味着享受不到任何作为国家员工的福利或补贴,计件的临时工资就是她全部的收入来源。

随着子女们都长大成人,高老太太对1980年代的回忆可以用苦尽甘来来形容,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又活过来了”。2009年,由于一场重病和手术,89岁的高老太太开始了不能自理的卧床生活,子女都有了各自的生活,纷纷远去,亲朋好友也渐渐不再来探望,每天除了伸手到床边的桌子够香烟的那一刻以外,高老太太已经很少翻身离开自己的床了。
在与高老太太一家和她本人的多次接触与交谈中,作者敏锐地注意到,高老太太的历史叙述似乎总是有所重复:不同时段和不同场合下的叙述,也往往有许多雷同的桥段。在艾华看来,高老太太的这种叙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验证的展示性实践与对一生艰苦、贫困与坚韧的宣示认可”(页69)。换言之,在她的个体化历史叙述中,大半生的苦难最终都将是有意义的,而她把这种苦难史的意义实际上赋予了将子女顺利拉扯成人这件事上,并通过不断复述自己一生的艰辛与不易,把那些“遭受不公义、无助、受难的故事转换成为有关坚忍、决心,乃至美德的证词”(页71),最终在个体化的历史叙述中,完成了人生自我意义的找寻与救赎。卧床后的高老太太对艾华半开玩笑地说过,说她自己已经活得太久了。这一方面当然是对自己卧床状态的无可奈何,但也未尝不是失去人生目标后失落情感的流露。
不同的个人记忆所组成的私家历史往往高度差异化,且与主流历史叙述并不完全吻合。比如,在主流历史叙述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1949年与1978年,在高老太太的受难史讲述中,并没有占据特别的记忆节点,反倒是若干“挨饿的时候”所形成的饥饿记忆,更加深刻地型塑了她所反复讲述的那段历史。她对政治并不热衷,也不真正理解,北平的和平解放并没有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她参加了“文革”时红卫兵在她家附近的一次批斗游行,但她自己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一场什么运动;改革开放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高老太太能买到的食物的极大丰富,但这也并没能改变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那两间平房的逼仄空间。总之,个体化的历史叙述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的异质与多元:它既非全然无法听到的庶民的声音,也不是具有霸权的主导叙述的抵抗者。普通人的历史一直都在,只是绝大多数时候都潜藏在宏大叙事的边缘,等待着有心人的发掘。

性别:男性气概与女性情感
在艾华看来,赵勇(Zhao Yong)是个典型的北京“爷们儿”。这种“爷们儿”,是一种难以精确描述,却又有迹可循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作者花费了不少精力去仔细捕捉这种“爷们儿”气质的特征,最终发现很难用好或坏来评价赵勇身上的这种性别特质。赵勇和他的母亲、妻子,还有养女,共同生活在大栅栏西街不足10平米的两间平房里。他主要靠蹬三轮车和摆摊维生,由于没有营业执照,很多时候不得不与城管打“游击战”,东躲西藏。不幸被扣车罚款时,他除了破口大骂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对作者说,城管扣车完全是“个人管理”:“他们说你没问题就没问题,如果你有关系有条件,他们也许会有些让步”(页86),否则一切免谈。
最吸引艾华的,还是赵勇与她聊天的方式。在作者看来,赵酷爱谈论“大事儿”:政治、中国与欧洲(或许由于作者是英国人)、道德、孝顺、子女抚养、佛教等,无所不包。当赵勇开始谈论“大事儿”时,他往往滔滔不绝,不愿意让别人打断,而且声量会逐渐增大。赵的长篇大论没有什么特别的逻辑,问到他最近工作怎么样时,他甚至可以谈到道德、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等。这种漫无边际的“侃大山”,是北京大爷留给许多人的一种普遍印象。许多新兴的短视频平台上,都有对北京大爷大妈的“采访”视频爆火,从而加剧了对北京人总是夸夸其谈的刻板印象。然而赵勇的故事却表明,对道德、宗教、政治等“大事儿”无所不知的阔论,与现实生活中有限的人际接触和经济基础是有着鲜明的对比与反差的。无论赵勇的个人哲学(personal philosophy)听起来多么高深(或故作高深),其根基也不可能超过他所成长的大栅栏社区所能提供的日常生活经验。
在艾华看来,这种思考大事的方式,是赵勇对“拒绝屈服于他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磨难”的一种情绪宣泄(页101),也是他维护自己在地方社区中的权威与面子的情感手段。这种对赵勇“男性气概”的文化人类学解读,使我们顺利地发现潜藏在大栅栏底层居民“侃大山”背后的一种充满张力与矛盾的生活方式:当作者与赵勇谈话而赵的母亲希望加入时,赵勇往往粗暴地阻拦母亲加入:“我们说大事儿呢,您不懂。”但这并不妨碍他坚持多年如一日地照顾行动不便的老母,并坚持认为孝顺是第一美德;赵勇十分怀念他小时候的邻里关系,那种不分彼此的互助型亲朋好友圈子,因而抱怨现在身边年青一代的冷漠与邻里之间的距离感;在赵勇参加的一个练习武术的团体里,他会为了“面子”而特意邀请外国面孔的艾华加入学习,以增进其在武术团体里的威望与谈资。而当他主动提出请作者吃饭,却发现餐馆的价位明显超出他的承受能力时,只好悄然放弃本能“有面子”的机会——抢买单。
对于赵勇与和他相似的许多大栅栏中年男性而言,像个爷们儿一样,有时很简单,有时却很难。

当然,更加艰难的或许是华美玲(Hua Meiling),她是作者唯一有机会长时间单独接触的中年女性。像多数大栅栏的老居民一样,美玲的童年也难称幸福。她从小叛逆,青少年时常与所谓“坏孩子”在一起玩,在改革开放初期属于可归于“不良社会青年”的一类。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因抢劫被判了7年,出狱后很快病逝,美玲认为他是一个毫无人性温暖的男人。唯一的女儿则似乎比她小时候更加叛逆,母女间的争吵与矛盾往往一触即发。但女儿无疑是这个失去丈夫的女人的生活重心,尽管不是全部。当作者成功成为美玲的倾吐心声的对象后,她很快了解到属于美玲的情感秘密:一个叫李大胆(Brave Li)的男人,在她丈夫去世后不久成为了她的“相好”。美玲喜欢李的“仗义”和勇敢,认为他是关心和保护她的,“他有很强的正义感,做事直来直去,所以当我认识他以后,我感觉我可以生活得更快乐。世道太艰难了,我看不到出路,但他可以拉我一把”(页113)。
这种吸引美玲的仗义,或者说另一种“男性气概”,尽管为她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与保护感,但对于她的邻居而言则显得不那么友好。一次醉酒后,李大胆与美玲的邻居发生了争执,最终发展成大打出手,李用刀子划破了她邻居的脸,之后便迅速逃跑了。真正让美玲与她的情人产生危机的,是一次意外怀孕。当她把事情告诉李大胆时,李表示自己不可能养活得了一个孩子。对作者讲到这里时,美玲显得绝望而又无助:“男人没一个靠得住。”
在艾华看来,美玲的生命史是游走在“内”、“外”之间的:对内,女儿是她生活的全部重心,也正因此,她的掌控与命令激起了女儿剧烈的反抗、母子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对外,生计的维持需要她骑自行车到很远的餐馆和商店去打工,尽管这种谋生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给女儿提供经济基础。然而,美玲的情感世界,究竟归属于内还是外?李大胆能够占据她生活世界的多少比重?对于这些问题,艾华并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她对性别视角的引介,对我们理解更好的理解底层人群的性别特质与情感生活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帮助的。

地域:归属与疏离
大栅栏社区的居民,并不都是“老北京”。在市场化改革与人口城市化流动加速的21世纪,情况就更是如此。李福英(Li Fuying)是从陕西北部农村地区来京务工的“外地人”。1997年,由于得罪了家乡当地的黑恶势力,李在当地的小生意难以为继,他决定到北京碰碰运气。在打探到工作机会后,他决定带上妻子张元晨(Zhang Yuanchen)一起来闯荡。张很快找到了一份侍候老人的家政工作,月薪300元。但李福英自己只能找到工地上日结的零工,且往往无法按时拿到工钱。由于付不起哪怕是最便宜的房租,李经常要睡在大街上。像许多其他的务工人一样,晚上他经常在西客站外的广场上睡觉,但执法部门随时可能将他们赶走。
终于,李福英找到了一个比工地零工要好的工作,蹬三轮运货,每月能挣到450块。但新的危机随之而来:他被警察带去了收容所。作为“盲目流动人口”,等待他的结果是遣返原籍。历经艰难,李再次从原籍返回北京。然而,他还得从事夜间装卸工之类的工作,从头开始他的谋生之路。由于没有多余的钱给看守人员“好处”,李福英经历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折磨。
2000年前后,李福英和他的妻子终于在大栅栏的一处大杂院租住了一间平房,不用再过露宿街头的生活了。李开始蹬三轮车,带着从全国各地前来观光胡同生活的游客,穿行在大栅栏附近的街巷之中。坐车的人,在畅想这就是提笼架鸟的“老北京”生活的地方,感叹对高楼林立生活的厌倦与对平房生活的渴望;而蹬车的人,则很可能在期盼尽快挣够钱,早日搬离这个早已是外地谋生者聚集、没有上下水的逼仄生活环境。

对于像李福英这样的“蹬三轮儿”的人,最头疼的是如何应对随时出现的会罚款和没收三轮车的“城管”们。在李福英看来,这些人是“欺软怕硬”的。他跟作者讲道,一次一名东北的三轮车夫被抓到要没收车子,但他很快召集了他的东北老乡们一起出来,将执法者暴打至头破血流。之后再遭遇时,城管往往会选择性地抓其他人。在暴力与秩序之间,李福英的生存空间更显艰难。
作为大栅栏社区日益增多的“外来者”,他们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来自本地人的排斥。本地房东对这些外来务工的租客格外苛刻,有时故意多收电费,有时突然上涨房租。根据李的叙述,房东跟大栅栏社区派出所的民警关系很好,但他非但不帮助李协调归还扣车的事情,还暗中帮助他们截堵三轮车,为他们提供线索。房东夫人,则是另一幅面孔。当她需要李福英帮她用三轮拉煤气罐到家里时,往往笑脸相迎,礼貌有加;而一旦用不上他时,则当街见面都不会打招呼,仿佛他不存在一般。尽管来北京已有十年,但李福英和他的妻子很难找到任何对这个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李的妻子对艾华说道:“北京人是冷漠的。他们没有感情……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你……特别是在大栅栏儿。但受过教育的人不是这样的。”带着互相的不认可与距离感,在这个首都中心的边缘地带,外来者与本地人矛盾地共生着。
2006年,当作者第一次在李福英家中见到他们的儿子小李时,老李对儿子的介绍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与自豪。这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在河北一所大学完成了动画设计专业的学业;至少在他的父母看来,即将有着美好的前程。然而,最终令父母想不到的是,小李的美好前程是以与原生家庭的分离为代价的。小李于2012年结婚,他的妻子坚持不与公婆同住,甚至不允许他们到家里看一眼自己的孙子。年青一代划定了自己的城市生活圈和亲情的社交距离,但这一切在城市社会看似合理的法则,却令李福英和他的妻子感到人生意义的幻灭。被城管追得东躲西藏,为省钱睡在火车站广场的日与夜,或许对于他们而言还历历在目,但这一切奋斗的意义——儿子的前程,像一根断了的弦,突然失去了凭借。2015年底,李福英和妻子返回了陕西老家,几十年的北漂生活最终又绕回了起点。在北京,尤其是在生活最久的大栅栏地区,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域认同。没有特别的技能和学识,只有吃苦耐劳的他们在城市管理者和排外者的心目中,永远是不合时宜的“低端人口”。

“认可”:寻找边缘人
高老太太、赵勇、华美玲、李福英……尽管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与生活状态,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心的边缘人,被“折叠”在北京的“第三空间”。他们生活在首都的底层,他们的经历沉寂在主流叙述的边缘,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明言的:“我在本书中试图去感知大栅栏居民的个体记忆与他们过去经历的意义,以此来打破(trouble)一种底层缺位的历史叙述”(页12)。这种寻找底层群体声音的努力,尤其是背后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艾华发现,对于许多大栅栏居民而言,“获得认可”,尽管有时是虚无缥缈的一种情感,却比得到实用主义的物质利益更加重要。正是在瘫痪在床期间,高老太太向作者讲述了更多她在动荡的20世纪的种种经历,因为她感受到了这个英国人对她长久而真诚的关注;正是在艾华尽管感到尴尬,但还是答应赵勇去参加他的武术练习团体的那一刻,赵勇感受到了外国友人为他带来的“面子”;正是在与美玲多次单独的长谈中,作者发现了美玲只与她分享的情感秘密;也正是在多年来不断地重访李福英夫妇的过程中,作者获得了了解这对底层北漂夫妻对城市生活的疏离与对子女远去的绝望的机会。在寻找边缘人声音与历史的过程中,艾华自己也成为了他们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作者自己看来,她撰写本书的目的,正是试图去理解像这些形形色色的大栅栏居民一样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艾华希望她对底层北京的研究,可以被理解为一项有关找寻“认可”(recognition)的道德与历史的任务。这种找寻,是“一种重返底层民众所依附和从属的特定位置的认可感与权威的尝试”,并力图将“底层”安放在“构成既值得被叙述,又至少部分可能地被叙述的主体性位置之上”(页224)。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全书采用了一种学术著作中绝少采用的章节布局:除第一章是关于大栅栏地区历史沿革的背景介绍外,第二到第七章分别以一个人物为主人公进行故事叙述,同时又在不同人物故事的章节之间,加入了作者对该对象进行文化研究与人类学分析的幕间“插曲”(interlude)。换言之,只有在完整了解了每一章节主人公的基本生平后,才会进入作者主导的分析环节。在从一个故事到故事分析,再到另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分析之间,首都城市中心的边缘人故事的主体性得以完整呈现。

2019年后,早已被划定为“历史核心区”的包括大栅栏在内的许多老城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文物腾退”,北京电视台主办的协调“老公房”居民与政府协商腾退补偿费用的调解节目,被截成短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尽管这种协调于最终结果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媒体终于愿意为这些平时很难有机会表达自己想法的底层居民提供一个发声渠道,这件事本身是值得赞许的。因为表达观点的权力,与得到被理解的机会一样重要。我们需要倾听更多的声音,以便于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以及其如何发展至今的历史。正如一位历史学者向城市规划决策者所苦心规劝的那样:“一个有生机的城市,人口组成应该是多层次的,没有只有高端人口的城市”(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3页)。而一段有温度的历史,它的叙述主体也应该是多元的,因为这世上本没有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
安劭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澳门大学历史学博士。根绝人类学调查保护受访者隐私的研究伦理,文中所有人名均根据拼音直译。原文标题为“寻找首都中心的边缘人:评艾华《底层北京》”。
———
微信搜索“燕京书评”(Pekingbooks):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