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的夏天,诗人北岛从巴黎出发拜访朋友。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小镇上,他参观了法国具象主义大师巴尔蒂斯的故居。那座木制农舍式别墅在历史上留有姓名,曾接待了雨果、坎特伯雷大主教等诸多名流。数年后他在手记中回忆起,“这栋十八世纪的旅馆共有一百十三扇窗户”。
故居仅有一间陈列室对外开放,北岛在院内闲逛,路过一间马厩,一匹马正从窗口向外张望,马脸上有块粉红色的斑。他取出相机,在马侧视时按动快门——这幅名为「视野」的作品后来被发表在《书城》杂志上,算是北岛“有意识的摄影创作”的开端。那是他离开故土的第 15 年。

差不多又过去了 15 年,在北岛的摄影个展「重影」上,我第一次看见诗人的摄影作品。那年是 2019,北岛正好 70 岁,他所创办的《今天》杂志已行过半百。这些游过的时间里,他与年龄带来的疾病做对抗,给孩子选编诗歌集,创办“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从未停下创作。
在那次个展的对谈分享会上,嘉宾顾铮将北岛的摄影风格提炼为某种“志异”的超现实主义,策展人沈祎则聊起自己观察到,摄影与诗歌之间存在的微妙关联,北岛在现场回应说,自己“真的是业余的摄影师”,只是“需要打发时间的方式”,摄影是没有门槛的,不过,“你要找到自己的眼睛”。

初代斜杠青年
.png)
事实上,北岛的摄影和写作是同步开始的。
1970 年代初,还在当建筑工人抡大锤的北岛,因为经常给工地师傅们免费拍照,被钢厂看中,许给他一份“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摄影展览工作。那时他正好想要创造机会写完一部中篇小说,就和宣传干事谈条件,在密密匝匝的集体生活中,给自己争取到了两米见方的木板房——一间能在地下状态创作文学的暗房。
那会儿,文学创作和摄影在他的生命中,就像《白夜行》中的两个原型那样互为掩护,构成明暗。根据北岛自己的分享,最初迷上肖像摄影“主要都是给女孩子拍肖像,也是动机不纯(笑)”,后来创办了文学杂志《今天》,与文艺圈的众人逐渐相熟,接触到一些真正的摄影师和摄影作品,“自己知道没戏了”。
虽然他一直称自己的摄影停留在业余水平,他的“非专业摄影”与普通的玩票也有直觉上的不同。他总在说,40 岁开始漂泊,作为一个“国际流浪汉”,与世界上的每一种生活擦肩,既是亲历,又是旁观,免不了那种永恒的游客感。在墨尔本一个闭锁的博物馆前,他沮丧、忧郁,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走到天涯海角了”。玻璃门上的水帘能隐约透出些室内的灯光,他望着玻璃前的自己,把相机放在胸前拍了几张。这张照片被命名为「家」,“因为那感觉特别像我梦中的家,很虚幻,很神秘,只有模糊的房子和窗户,还有一点微弱的灯光”。而现实中的家早在时间磨损里失去原来的意义,他曾在某次采访中提到,“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真的还有乡愁,那也是浸泡在某种文化记忆里的,在他的诗歌里、摄影里,他愿意一遍一遍复刻梦中的家。

语言总在万事万物的“是”与个体表达之“是”中间搭起某条管道,北岛的摄影语言是他有意识地萃取提炼,属于他自己的。如果非要给作品进行共性归纳,它们都有距离感,大多是局部,彩色,无后期处理,物象背后总像存在某种意象,有种扑面而来的阴郁,朦胧,总之“很北岛”。
早期《书城》刊登他的作品时,总会鼓励他写些摄影手记。起初他会写几笔环境与气氛,避开阐释作品,后来连这也写得少了。2008 年底,他带着一种重返的伤感走在荷兰海牙的火车站,忽然被光斑晃住一瞬,他回忆,当时沉郁的心情被触拨,“火车站天棚有块玻璃被打碎,露出现代化建筑的一角,恰好也是玻璃窗。内与外、明与暗、破碎与完整所形成的对比,让人想到存在的遮蔽与呈现,想到记忆的选择与盲目,想到命运。”他取出相机,把画面拉近,“拍完照片,我感到如释重负。”

摄影是即兴与偶得的,且总是与当时的某种情绪有关,“情绪也是记忆的一种”。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窗户是北岛尤其钟爱的意象和主题。窗户或许是画框中的画框,是抵抗外部世界但又透光的墙,是禁锢与冲破,框架或疏离,他说自己反对阐释。世界对于答案总是闭口不言,而对于自我和被摄对象的互认与相遇,拍摄是用瞬间来呈现过程。
被日常生活所熟视或漠视的,在一双游荡的眼睛下变得陌生化,进而被带领,逼近某个暗部。北岛自己形容,自己关注的总是在距离感下,一座城市“幽灵”的部分。在新德里,他拍下逆光中错落的经幡;美国白沙国家公园里,他在石膏粒组成的沙丘上拍下一种头发丝一样的植物;在夏日的诺曼底,他记录垂钓者背后静止的灯塔;还有许多的水波、光斑、位置与轮廓暧昧的器物与人物……2013 年在米罗美术馆,他拍下两束重影交叠的灯光,取名「影子」,那年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主题被定为「岛屿或大陆」,这张照片最后成为了出版物的设计主视觉。
顾铮说,看北岛的摄影作品,读出一种与光明的对立。在“凝视深渊”忽然成为网络热词的当下,始终带着审视打量着阴影、也打量着“残忍的光明”的诗人,已经把自身投掷进这个短语里,在暗部踽踽独行数十年。这期间,他说过“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也说“诗歌里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语言,第二个层面是空白和沉默,第三个是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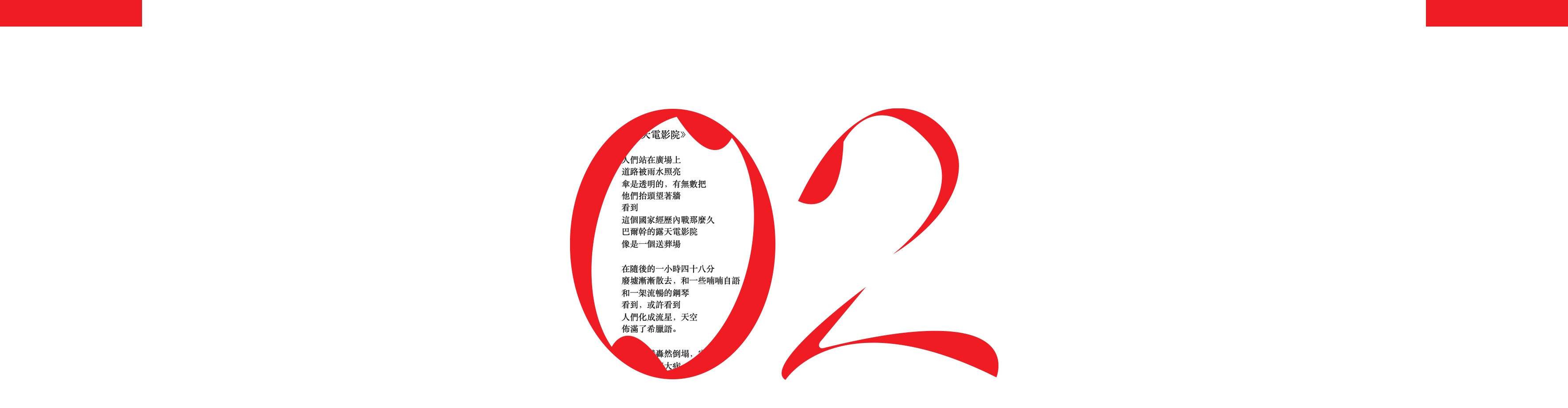
所谓「文学性」
.png)
几年前,北岛因为操办香港国际诗歌节而累倒,诗歌创作陷入停滞。策展人沈祎观察到,病中的诗人以一种强大的意志力与疾病对抗着,在语言表达能力受损的情况下,摄影并未被扼制,反而因生命体验得到拓宽,同时开始转向绘画,“他用了另外一种语言,或者说迁徙到另外一种语言去创作”,“顾城有一句话,‘当语言停止的时候,其实诗歌前行了。’”
沈祎和北岛结缘于“香港城市文学节”,那时她仍是在校大学生,她的作品拿到了新诗组冠军,担任该奖评审的便是北岛。在获奖人介绍里她说——未来的理想是能做一个摄影师或电影导演。

她的确那样去做了。从 2009 年开始,她在各国举办摄影展,2014 年开始电影创作。2020 年,她成了“一个一意孤行要拍亏本文艺片的中年人”,担任电影《掬水月在手》的制片人,与符号学背景的导演陈传兴一同,让更多人知道了叶嘉莹先生,与她口中的「弱德之美」。
她曾分享过早年访谈与撰稿时的一个观察——“我发现周围的诗人拍照都拍得特别好,或者我发现很多拍照拍得好的摄影师其实写诗也写的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联系。”经由同样热爱摄影的诗人王寅介绍,她认识并采访了北岛,两人逐渐成为好友。2012 年,她成功策划北岛首个摄影展「零镜」。
我与沈祎在繁忙的交流活动间隙见面,她讲话不快,但表达极密。聊天中她提起北岛摄影最初的那间暗房,黑暗给他的创作带来某种庇护,而诗人的作品中,凝视黑暗的决心也贯穿始终。她决定将最新的这次「重影」展厅布置成黑色,而有趣的细节是,色板上她最终定下的那款黑,名字就叫 secret dark。
沈祎平时仍写诗,爱在豆瓣碎碎念。在最初诗歌大赛获奖后,北岛也曾问她,你这样热爱文学,是否有什么家学渊源?她努力回忆,自己的父母都是理工科出身,着实没有什么直接渊源可言。后来到了三十岁,一种明确的自我意识忽然造访。父亲将一份旧日手稿作为生日礼物赠给她,手稿的主人是她的祖父,文革时祖父过世,他的文字大多佚失,家里也极少提起。如今躺在沈祎手上的这份是混乱年代家里偷藏下的唯一一份文学小说手稿。后来,《东方早报》的民间文学板块刊登了那篇小说,沈祎还记得,小说的名字叫《秋天的忧郁》。“我就是出生在秋天的人,他怎么会知道,他未来会有个孙女,出生在秋天?生命跟生命之间的这种不可知、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奇妙的。如果我的血液里真的有那么一些文学的基因,或许就是我的爷爷通过某种方式,他的灵魂的某个碎片掉落在了我身上。”
是否文学性会有某种命运般的选定和联结?诗人北岛无法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拍照,他的创作冲动仰赖某种陌生带来的刺激,但对诗人沈祎笔下的香港,他投以最真的首肯与欣赏;艺术家北岛与艺术家沈祎聊文学生涯,情绪与记忆,瞬间与张力,还有生命中的女性。随后笑着安慰她,“你的问题别那么严肃”。而沈祎总会提醒他,“拍照记得留底片”,以及,“微信发送记得点原图”。
“抗争性是西方哲学所探讨的人类生存的本质,”在谈及北岛的自我与对立精神时,沈祎提起杜甫、罗兰巴特、鲍德里亚和海德格尔,她甚至接近完整地背出了加缪的一段话以回应我的某个提问。
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通常情况下,选择献身艺术的人都曾自视与众不同,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与众不同往往就扎根在与所有人的相似中。艺术家就是在自我与他者不断的交往中,在无法抽离的群体中慢慢锤炼自己。因此,真正的艺术家看重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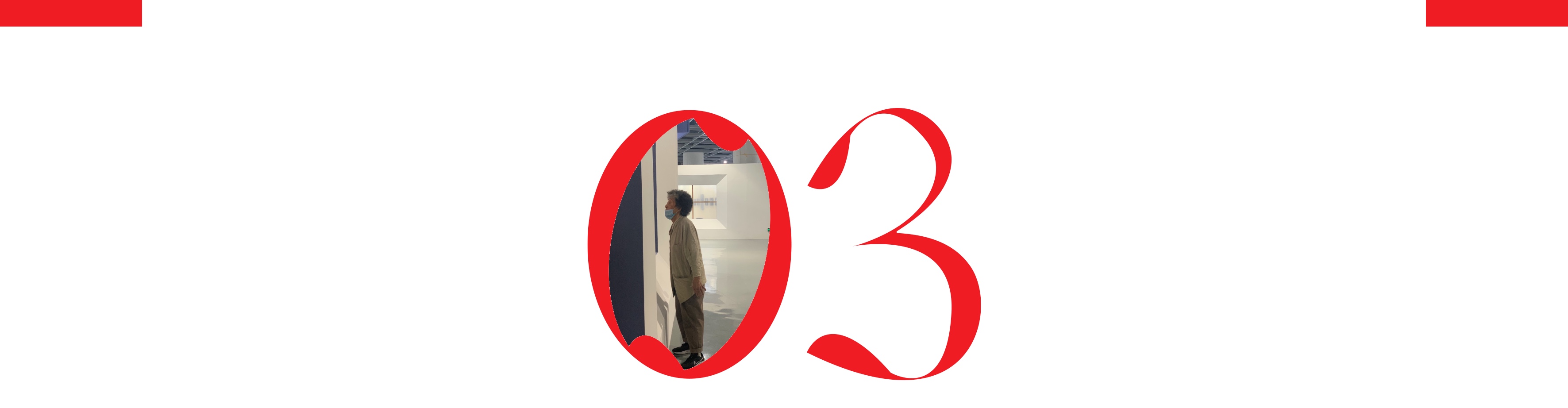
每个人都追求某种纯洁
.png)
在这次厦门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我认识了一位陈奶奶。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午后的西餐厅,她穿过笑谈的众人,站在排满酒瓶的吧台前喝一杯牛奶,喝得认真、安静,一旁的服务生同样认真又安静地擦拭酒杯,待她喝完,应她要求为留有奶渍的杯子续上清水,喝完那杯水,她道了谢,转身缓慢地离开。
那天的晚宴上,我与三影堂的工作人员同席,又再度从她们口中听到这位奶奶的故事。独居的陈奶奶已经年满七十,是位马来西亚华人,年轻时在北京做英语老师。如今她一个人在厦门,每天早上自己做餐 brunch,随后搭地铁或是公交来到摄影展,一呆便是一下午。展厅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已经对她十分熟悉,她们说,展厅里的每个字陈奶奶都认真地读过不止一遍。在厦门,陈奶奶已经成为各类艺术节展的常客,出现在许多年轻人的打卡帖中。
在「重影」的策展人导览开始前,陈奶奶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这次,她背了一个帆布袋,沈祎在对摄影作品逐一介绍时,奶奶站在她的身侧,良久注视着每一幅经过的画片。导览结束后,她走向沈祎,指着一幅名为「降临」的作品问,Why the name Arrival?
.jpeg)
那是北岛隔着一道门拍摄的小儿子的模样,沈祎向奶奶说起背景,还有作为名字灵感来源的电影。奶奶又走向「梦中时刻」,站在布满鱼群的画面前,她说,这让她想起莲花,想起浮萍。
(直到从盐碱地的白纸上看到理想《履历》).jpg)
她还说起从前在街道上无意记下的两个画面。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环卫工人,正在用地上的水清洗双手,“他在用地上的脏水洗手,他想变得干净”;还有一次,在堵车时她注意到路边走过一个流浪汉,就像从煤矿里刚走出来那种脏,头发和手像枯枝,整个人像一颗移动的枯树。沈祎久久看着他,看他走过一个小店,店门口杆子上扯了一根绳,晾晒一排白毛巾。这个人走上去,把脸埋进了一张毛巾里,“他忽然鲜活了,整个人闪耀了起来”。
后来,她把流浪汉写进电影剧本。在与导演李霄峰的多次合作中,她都坚持在故事里埋下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引。《少女哪吒》里,晓冰不是自杀,而是去向一个遥远的地方;《灰烬重生》里,两个少年会在决定交换杀人的那个月夜相拥跳舞,每个人都在追求某种纯洁,“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对干净,对纯真自我的向往,是永恒的。”
三毛曾在打给好友小熊的电话里说,在我的剧本里,每个人物都有一个致命伤。
就像在这个有限而不足的故事里,写到三个不同的个体,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行路,人生体验各异,而每个人都显示一种相似的质地。精神故土纯洁一片的人,在梦里,照片里,诗歌里,电影里,绘画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返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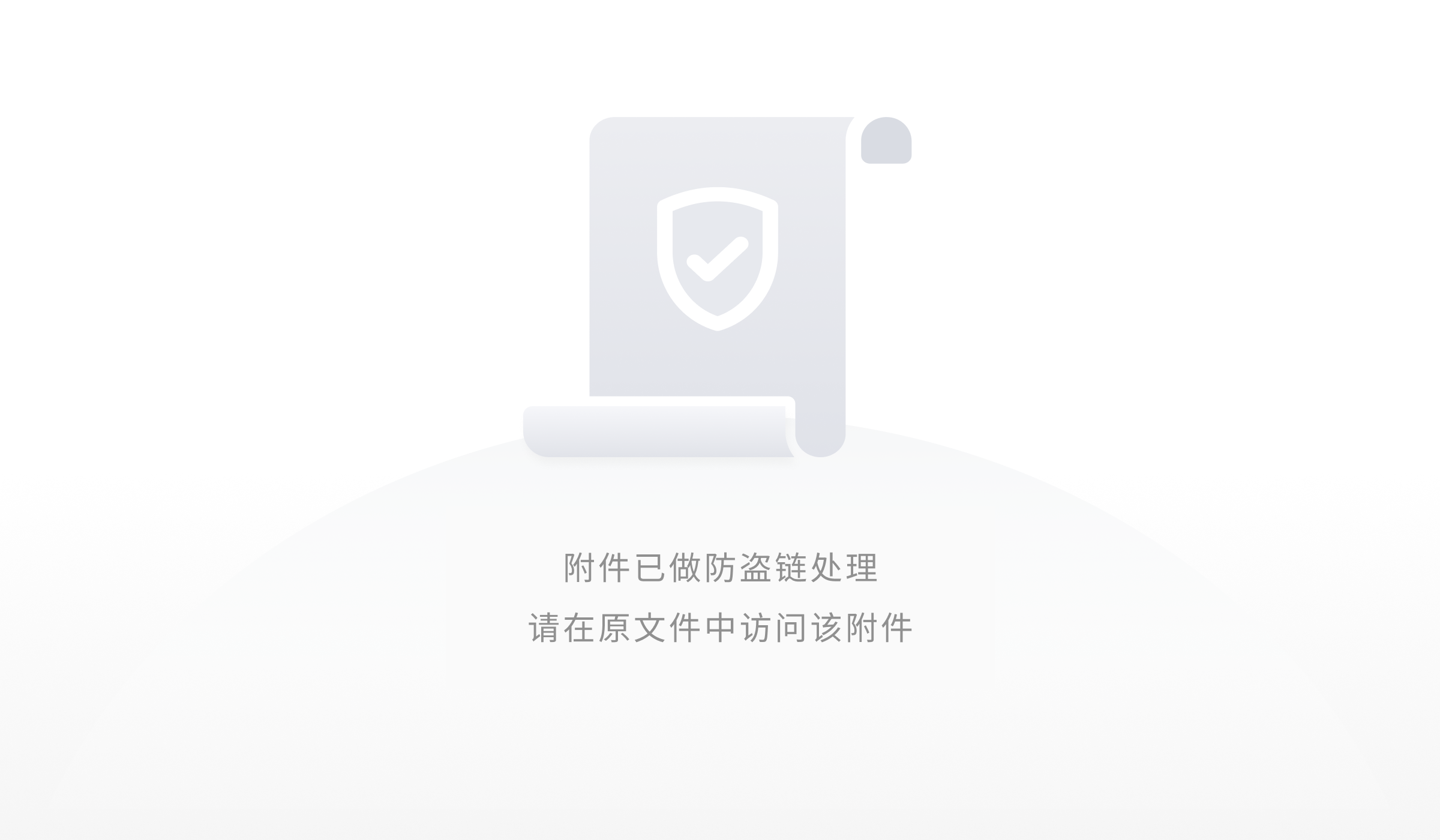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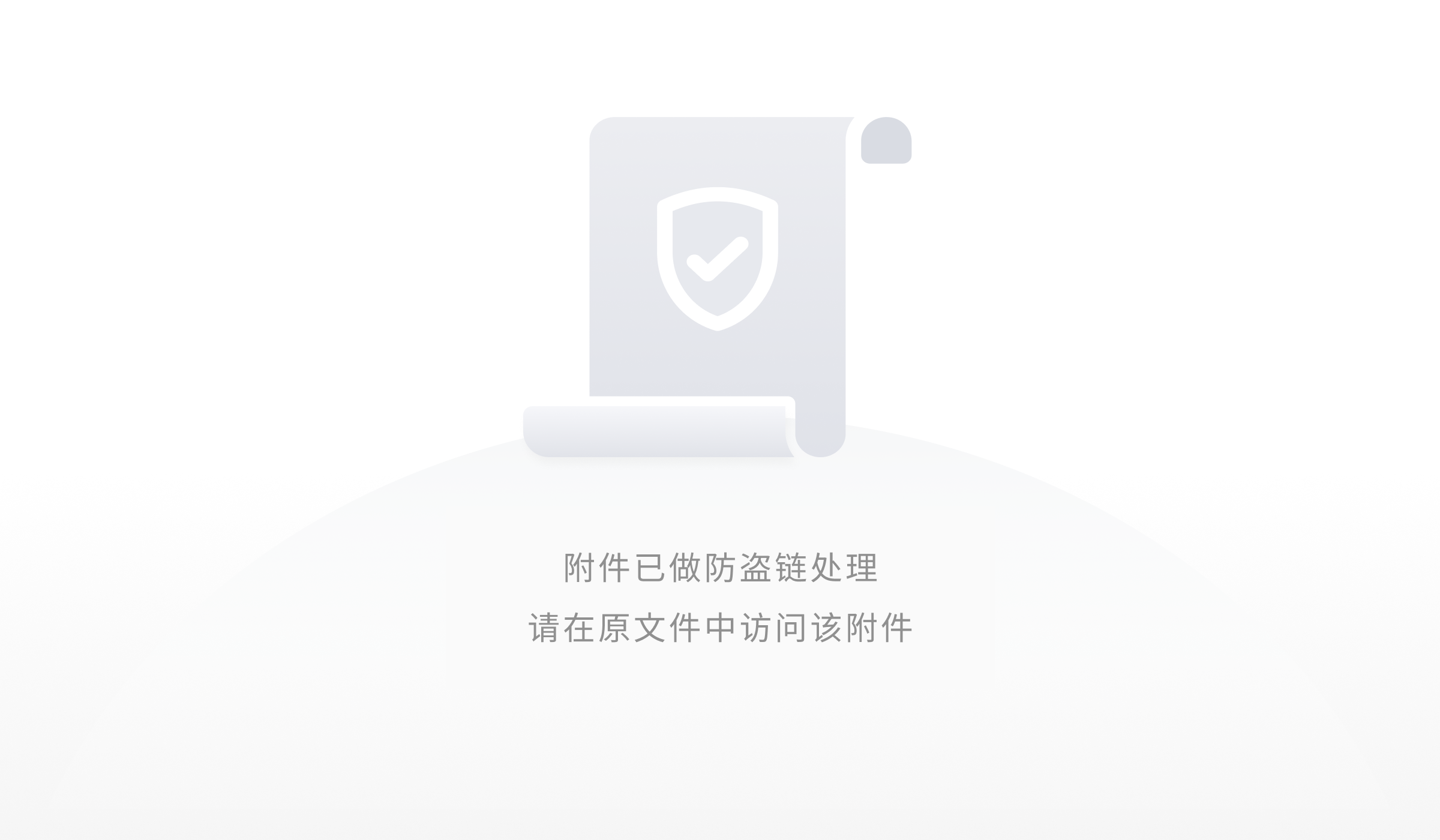
诗人北岛,写作的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如今,他仍时不时在豆瓣发布自己的诗作。他近期创作的长诗《歧路行》选段在个展现场由文字投影展示。展厅一角有一副桌椅,椅子上由北岛亲手刻下一行字:
「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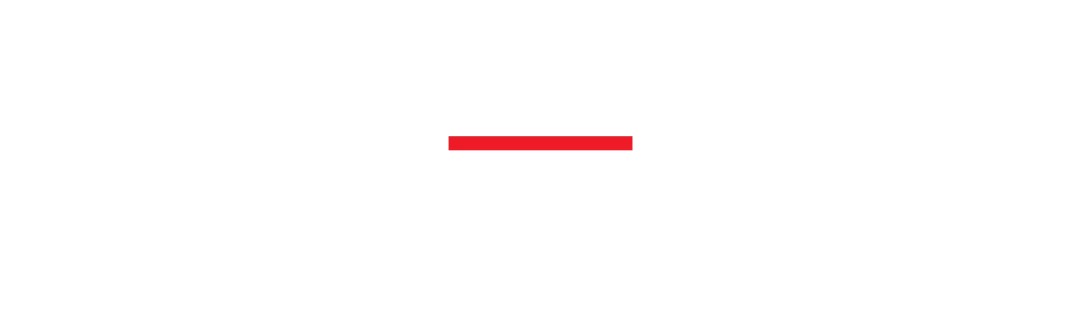
2021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已于厦门开幕。
今年摄影季将呈现 30 场展览,来自法国、新加坡、巴西、捷克、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等地超过 110 位艺术家的 2000 余件作品。“无界影像”单元呈现了艺术家在媒介(印刷、视频、数码、装置等)和多元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展开摄影的多元跨界可能。本年度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有幸邀请著名诗人北岛、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小东和当代艺术家赵半狄展出作品。
展期持续至 2022 年 1 月 3 日。
参考资料:
《重影》,北岛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ICICLESPACE 之禾空间:活动回顾 | 诗歌与摄影——北岛、顾铮、沈祎对谈分享会
南方人物周刊专访——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
文中展览配图授权自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文中诗歌配图授权自沈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