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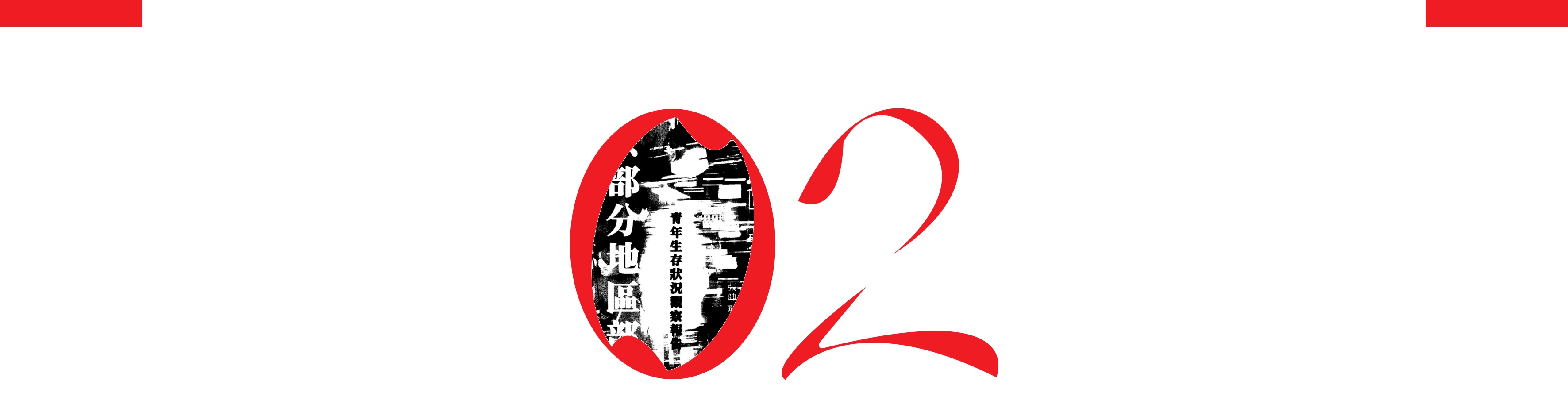
.png)
辞职后,我来到了大理。这个集中产(亚逼它爹),和嬉皮士(亚逼老祖宗),两种气质之大成的宝地,顺理成章地进化出了一种不同于京沪的亚逼新品种——三和亚逼,顾名思义,就是自嘲自己过着像三和大神般“挂逼”生活的亚逼。
作为一个一眼就能识别出亚逼气质的局外人,潜入大理的第二天,我就通过对方光源体的头像,爱与和平的微信签名和迷离梦幻的朋友圈背景图,在一个社群里加上了本地亚逼的微信,并在两天后来到她打工的烘培店里,蹭着她和女友的小电动,听着文学亚逼一晚上卖了 8 本诗集的好消息,参加了一场亚逼内部的日常聚会。
在一场司空见惯的马路牙子聚会上,除了拿出手机轮流播放虾米歌单、捏着鼻子轮流喝烈酒、分食咪咪等膨化食品和辣条之外,聊电影成了最终的硬通货。这个喜欢今敏,那个酷爱周星驰,这个去过 FIRST 影展,那个刚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回来,而我心中的文艺片三巨头——侯麦、伍迪艾伦、洪尚秀,更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和共鸣。
在喝高了准备转场的夜晚,月黑风高,三个蹦迪刚认识的男女挤在的士后座上,吐露“我没有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这种酒醒了矢口否认的真心话时,往往会顺带聊起那个深藏心底不轻易予外人言的电影梦。
我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就叫它“北京亚逼生存报告”吧(豆瓣条目为《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那就是我想拍的纪录片。挤在我旁边的短发女孩从北京来,淡定地说导演她认识,下次来北京,给我介绍一下。

当时已经离职三个月的我刚开启自由职业,正愁在大理找不到选题,酒醒了以后,我以采访的名义认识了张帅。

.png)

金刚和朋友们的马路聚会,出自《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png)

梁倩和朋友在游船上,出自《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金刚,出自《2020年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

.png)

看完后超级喜欢这部片子的观众制作的海报

拍片记得开发票的张帅
